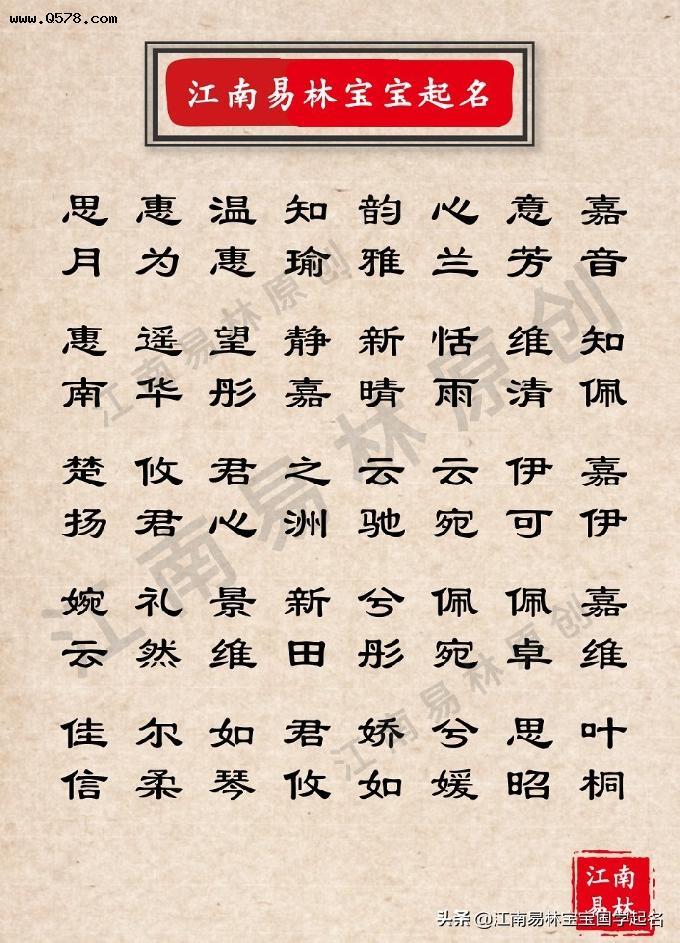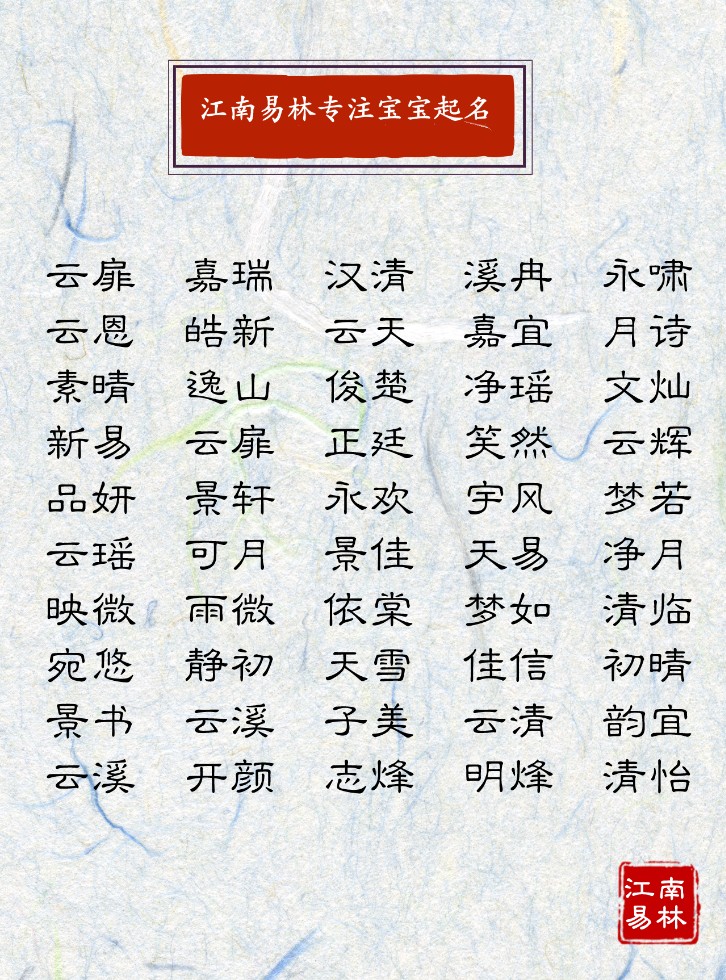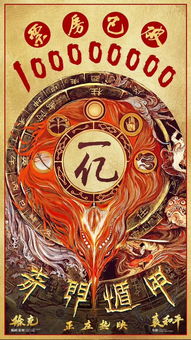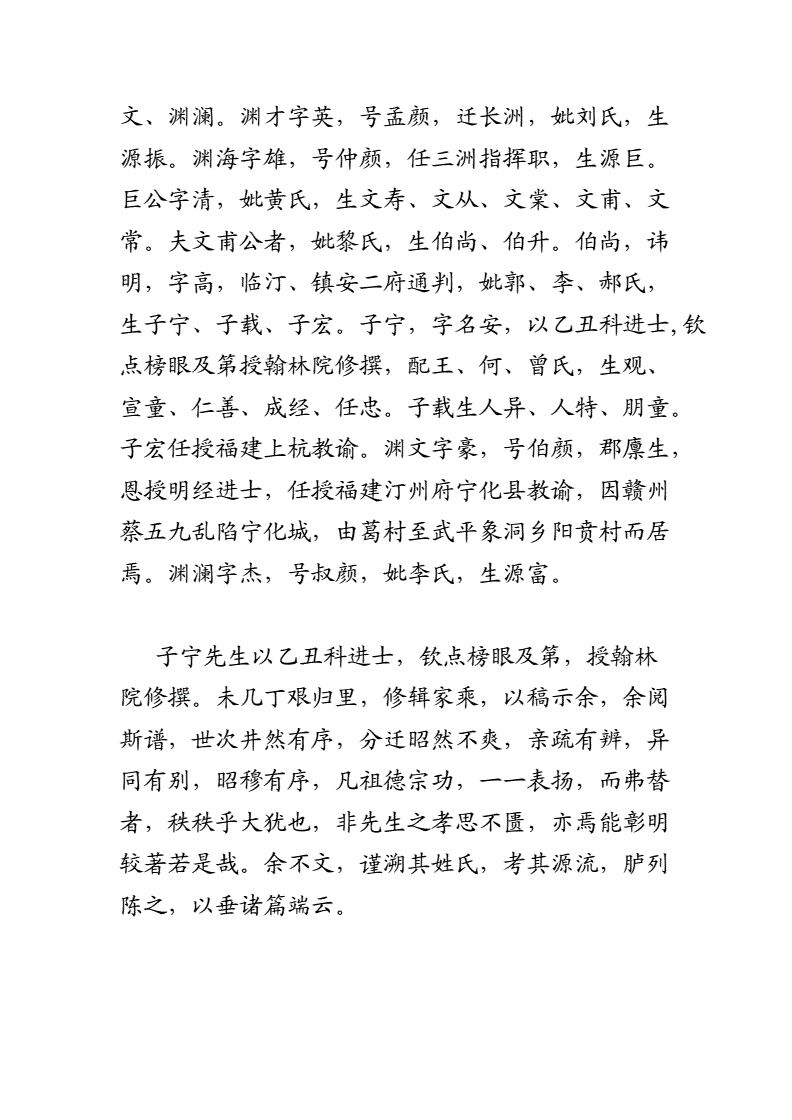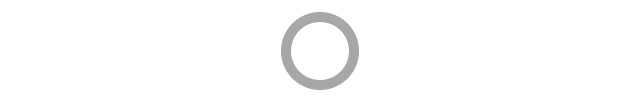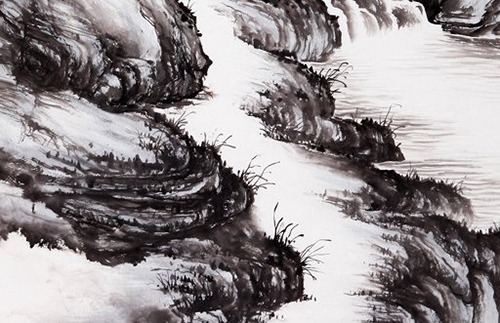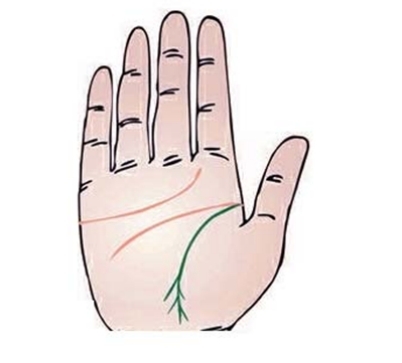《国殇》《礼魂》和楚国战争失败罪
- 百科
- 5天前
- 675
作者简介:黄震云,男,江苏省灌南县人,文学博士,著名文化学者,诗人、书法家。原为江苏省政府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333工程),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兼常务副秘书长、中国辽金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辽金元文学学会副会长 ,九三学社中央思想建设中心研究员、教育部同行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等课题多项,获得省部级奖励六次。从大学四年级开始发表学术论文,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楚辞通论》《辽代文史新探》《辽代文学史》《经学与诗学研究》《法治文学研究》《立法语言学》《名家讲解山海经》《汉代神话史》《左传整理》《中国名画考古研究》等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
命理师念鲜的微信:nianxiangege
内容提要:夏、商、周和楚国有军事法。既然有军事法,可以确定当时的楚国有战争失败罪,说明《国殇》不可能用来祭祀战争失利或者战死的将士。根据《九歌》的属性和具体内容来判断,此诗应该是纪念楚怀王的礼乐作品。
关键词:《国殇》;《礼魂》;战争失败罪;礼乐

关于《国殇》和《礼魂》殇谁礼谁,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普遍认为这是描写楚国战争、歌颂英雄的爱国主义作品。但是,说它们记录了当时真实的战争,则只是后代人用爱国理念推测出来的。《国殇》说: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如果将《国殇》理解为实战,存在着一些无法说通的地方。第一,《国殇》是《九歌》中的一首,而《九歌》是一个系统的祭祀神灵的礼乐体制,最后附上一篇反映楚国实战的作品,显然不合体制和主题。第二,在“左骖殪兮右刃伤”的紧张时刻,偏偏要“埋两轮兮絷四马”,“絷”就是系,也就是将马拴起来。这是什么打法?听起来就不靠谱。第三,如果诗歌赞美将士“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可能不可凌呢?如此种种,无需多举。
《九歌》是一组古老的礼乐。《左传·文公七年》所记载:“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尚书·大禹谟》指出:“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都肯定《九歌》为表现功德的作品,与描写实战没有关系。
现存《九歌》十一篇。《韩诗外传》指出,大禹为了满足天下对舜的崇拜,将《湘君》《湘夫人》编到《九歌》中,这是《九歌》十一篇的原因。可以认为,《国殇》不可能是描写楚国实战的诗歌,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先秦时代,不把这些战死的将士视作英雄,相反还要治罪,所以不会有歌颂他们的作品出现。根据史料,夏代就已经制定了军事法,其中就有不能完成任务将受到严厉惩罚的战争失败罪。《左传·昭公六年》载: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
夏商周时代分别有《禹刑》《汤刑》《九刑》这样的法律。《尚书·甘誓》《史记·夏本纪》等记载说:“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竹书纪年》作: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由此可知,夏代制定法律的人是皋陶。夏启的《甘誓》类似于战争法,强调必须执行军事命令,还制定了奖赏措施,就是打赢了要在祖庙进行庆贺奖赏,打败了则要在社坛前杀头,家属沦为奴隶。
夏朝还有监狱。《竹书纪年》说:“夏后芬三十六年作圜土。”芬是启以后的第七个夏王,他建筑圜土来囚禁罪犯。圜土是圆形的土牢,把罪犯圈围在里面。《史记·殷本纪》说: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後后,至周封于杞也。
夏台是夏朝制作的监狱,和圜土的囚禁对象有一定的区别,但都是监狱。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以上材料分别见《尚书》和《史记·殷本纪》,表示商汤攻打夏是替天行道,同时要求将士必须全力以赴夺取胜利。如果获胜将重赏,若打败了则被孥戮。“罔有攸赦”,也就是说打败了要问罪,全部杀光,家属沦为奴隶。这一奖赏制度和夏朝的战争失败罪几乎一样,已经成为定制。
周代传承了夏商的战争失败法,但相对夏代和商代而言似乎更为具体。《礼记·檀弓上》卷八说:“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又《尚书》记载鲁侯伯禽征讨淮夷和徐戎,作《费誓》:
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敹乃甲胄,敿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马,杜乃擭,敜乃穽,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汝则有无馀刑,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
由此可知,周代已经将战争失败等军事法作为常刑,奖惩胜负以外,还对运送粮草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这方面的例子在西周和东周都有。《竹书纪年》记载说:“厉王无道,戎狄寇略,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史书对战争的记载往往止于只说到胜负,很少涉及到战后事宜,但也不是没有蛛丝马迹可寻。今检《后汉书·西羌传》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伯士死和军败是因果关系,无疑伯士死于战争失败罪的裁决。即使是在周幽王乱政、礼乐崩坏的时代,战争失败罪仍然是有效法律。又考《左传·桓公十三年》说: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推断当时的战争有专门的刑法。鄢陵之战,莫敖惨败自杀,而战后对战败者的追责不仅仅限于主帅,“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就是说在冶父进行集体审判。楚国应该是接受了周代的刑法制度,制定了自己的军事法。又《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得臣。”《左传正义》说:“子玉违其君命以取败,称名以杀,罪之。”君命就是指出兵的命令,打败就是违背君命,也就是《甘誓》中说的不用命,罪之就是法办。又《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曰:
薳越曰:“再败君师,死且有罪。此年秋败於鸡父,设往复败为再败。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缢於薳澨。
薳澨,楚地。再败君师,死且有罪就是死后问责,即使战死了,也是要问罪的,可见战争失败罪是非常严厉的法律。西戎霸主秦国也实施了同样的制度。《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
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
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隳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
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文嬴知道,孟明视等是秦国的重要将领,如果失去他们,对秦国十分不利。因此,借口战争失败罪,告诉晋国人他们三人回去将会受到严惩。这说明:一是战争失败罪在晋国和秦国都存在,因此借口容易成立;二是战争失败罪审判时会有国家利益层面的考虑。几位将军很重要,秦国是务实的国家,不会杀害他们。《吕氏春秋·高义》记载了一则楚国将军躲避战争的故事:
荆人与吴人将战,荆师寡,吴师众。荆将军子囊曰:“我与吴人战,必败。败王师,辱王名,亏壤土,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王而遁。至于郊,使人复于王曰:“臣请死。”王曰:“将军之遁也,以其为利也。今诚利,将军何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后世之为王臣者,将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遂伏剑而死。王曰:“请成将军之义。”乃为之桐棺三寸,加斧锧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数至也。
由上可知,楚国有相对完备的军事法,战争失败罪的设立和形成历史悠久,楚国接受了相关的律条,并有自己的考量。桐棺三寸,加斧锧其上是尧舜时代的象性制度,历史更为悠久,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制度。战国时期楚国的战争失败罪规定战死同样是犯罪,如果逃跑则可以免于刑罚。那么,《九歌》中的《国殇》显然不可能是纪念阵亡将士之作了。究其原理,楚人认为,打败有罪,死于战事,为恶鬼。
那么,《国殇》纪念阵亡将士的依据和来源是什么呢?这源于汉代王逸的章句,认为殇指死于国事者,但并未解释具体死于何种国事,后人根据诗歌的描写,并结合历史上楚国在屈原时代发生的战争,推测为纪念卫国战死的人。古代的文献推理往往越推理越清楚,也就越远了。
《昭明文选》卷二十八鲍照《出自蓟北门行》“身死为国殇”,李善注:“国殇,为国战亡也。《楚辞》祠国殇曰”李善战亡之说也是出自唐代道德观念的判断,不足为训,但称《国殇》为“祠国殇”是说明唐代流传的《楚辞》版本依然是《祠国殇》。祠并非一般战死士兵所能拥有的待遇,士以下无庙,这是礼乐的规定。韶乐亦主要是庙堂礼乐,当然不会用在纪念阵亡士兵的场合。按
《小尔雅》卷五说:“无主之鬼谓之殇。《说文》云:‘殇,不成人也。年十六至十九死为长殇,十五至十二死为中殇,十一至八岁死为下殇。’《仪礼·丧服传》同《释名》,则统言之云未二十而死曰殇。殇,伤也,哀伤也……《礼记》云:‘宗子为殇,而死庶子不为后也。’”殇无疑有哀伤的意思。因此,楚国人仿照夏代人增加二女为祭祀对象的做法,加入客死他乡的楚怀王似无不妥。那么,按照习惯,祠这种祭祀方式是在春天,春祭曰祠。根据诗歌的内容,笔者认为这种祠怀王的方式是招魂复魄行为,是先秦常见的祭祀方式。
《礼记》有士丧礼,记载士丧问题,《礼记》卷十一有丧服,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
《传》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无受也?丧成人者,其文缛。丧未成人者,其文不缛。故殇之绖不樛垂,盖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无服之殇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殇,殇而无服。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死则哭之;未名则不哭也。叔父之长殇、中殇,姑、姊妹之长殇、中殇,昆弟之长殇、中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適孙之长殇、中殇,大夫之庶子为適昆弟之长殇、中殇,公为適之子长殇、中殇,大夫为適子之长殇、中殇。其长殇,皆九月,缨绖;其中殇,七月,不缨绖。
按经丧也就是殇,指的是十九岁以下死亡者,十六以上即为长殇,显然和军人的年龄不相匹配。换言之,殇指的是未成年人死亡,带有不幸的意思。因此祭祀不幸死亡的人也会用殇来表示。《穆天子传》卷六说:
天子乃殡盛姬于谷丘之庙。壬寅,天子命哭,启为主〔为之丧主……天子宾之命终丧礼,于是殇祀而哭,内史执策……敷筵席设几,盛馈具,肺盐羹,胾脯、枣、醢、鱼腊、糗、韭,百物,乃陈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壶尊四十,器,曾祝祭食……祭,祝报祭觞大师,乃哭即位,毕哭,内史策而哭……乐人陈琴瑟、竽、龠。
这是周穆王殇祀年轻的盛姬所举行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所陈设的实物和楚辞《招魂》中的结构形式非常类似。因此,《招魂》所招的无疑是楚怀王的魂。这里用的乐器和《东皇太一》中“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也完全符合。尽管这不是绝对的证据,但至少可以看到祭祀的礼乐规格之高,也符合传统的殇祀方式。《礼魂》也是大礼,和《招魂》当为一事的不同表现。
《周礼·春官宗伯下》云:“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薺,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所谓九德之歌,就是《九歌》,是用来礼人鬼的大礼。那么可想而知,《九歌》在当时祭祀的对象是可以作为国殇的人,当然是不幸去世的楚怀王了。就屈原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民间祭祀他应该没有什么兴趣,更不会为之出手。《周礼》宗庙礼乐核之《楚辞》屈原《离骚》云:“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乐。”又《楚辞·九叹·忧苦》云:“恶虞氏之《箫韶》兮,好遗风之《激楚》。”由此推之,与东皇和主神相配的祭祀对象,只有被骗死于秦难不幸的楚怀王了。王逸在《楚辞章句》认为“国殇谓死于国事者”,也是对楚怀王而言。又检《文献通考卷六十八·郊社考一》说:
太史公作《封禅书》,所序者秦汉间不经之祠,而必以舜类上帝,三代郊祀之礼先之。至班孟坚则直名其书曰《郊祀志》,盖汉世以三代之所郊祀者祀泰一、五帝,於是以天为有六,以祀六帝为郊。自迁、固以来,议论相袭而然矣。康成注二《礼》,凡祀天处必指以为所祀者某帝,其所谓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谓配天者亦非一祖,于是释禘、郊、祖、宗以为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盖在於取谶纬之书解经,以秦汉之事为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汉人崇之,六天之说,迁、固志之,则其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尝著《汉不郊祀论》,见所叙西汉事之後。
《国殇》祠(招魂复魄)楚怀王在诗歌中有明确的印证。关于四马,四马就是驷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按照西周的礼制,诸侯小国的地位和大国的卿大夫等同,那么祠楚怀王用驷马符合当时的规定。关于用矢招魂复魄。《礼记正义》引《左传》“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不听,公及邾师战于升陉”是也。注“时师虽胜,死伤亦甚”者,则传云“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是也。郑云此者,解“复之以矢”之意,以其死伤者多,无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必用矢者,时邾人志在胜敌,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复反。然招魂唯据死者,而郑兼云“伤”者,以其虽胜,故连言“死伤”以狭句耳。若因兵而死,身首断绝不生者,应无复法。若身首不殊,因伤致死,复有可生之理者,则用矢招魂。关于招魂复魄不具姓名,只言国殇。关于旌旗、车错毂、左骖等。《礼记正义》卷四十《杂记上》说:
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复魄,并明饰馆贵贱之等。此一经下至“庙门外”,论诸侯之制,今各依文解之。“诸侯行而死於馆”者,谓五等诸侯朝觐天子,及自相朝会之属而死者,谓诸侯於时,或在主国,死於馆者,谓主国有司所授馆舍也。“则其复如於其国”者,其复,谓招魂复魄也。虽在他国所授之舍,若复魄之礼,则与在己本国同,故云“如於其国”也。“如於道,则升其乘车之左毂”者,如,若也。道,路也。谓若诸侯在道路死,则复魄与本国异也。“乘车”,其所自乘之车也。其复魄,则俱升其所乘车左边毂上而复魄也。此车以南面为正,则左在东也。升车左毂,象在家升屋东荣也。其五等之复,人数各如其命数。今毂上狭,则不知以几人。崔氏云:“一人而已。”“以其绥复”者,绥,旌旗绥也。若在国中招魂,则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则招用旌旗之绥,是在路则异於在国,故云“於道用之”,亦冀魂魄望见识之而还也。若王丧於国,而复於四郊,亦建绥而复。《周礼·夏采》云“以乘车建绥,复于四郊”是也。注“馆主”至“生也”。正义曰:“馆,主国所致舍”者,按《曾子问》云“公馆与公之所为曰公馆”,是主国馆宾之舍也。云“与使有之”者,谓主国与宾此舍,使宾专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复用褒衣也。褒衣者,天子褒赐之衣,即下文“复用褒衣”是也。云“如於道,道上庐宿也”者,按《遗人》云“凡野都之道,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故云“道上庐宿也”。云“升车左毂,象升屋东荣”者,车辕向南,左毂在东,故象东荣。不於庐宿之舍复者,庐宿供待众宾,非死者所专有,故复於乘车左毂。云“绥当为緌,读如蕤宾之蕤”者,但经中绥字丝旁著妥,其音虽,训为安。此复之所用者,是緌也。緌,丝旁著委,故云“緌当为绥”。读此緌字为蕤宾之蕤者,音与蕤宾字声同也。以经作绥,故云“字之误也”。“绥,谓旌旗之旄也”者,按《夏采》云:“乘车建绥,复于四郊。”乘车,王路,当建大常。今乃建绥,无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旂。”後王文饰,故知有虞氏之緌但有旄也。云“去其旒而用之,异於生也”者,诸侯建交龙之旂,今以其绥复,是去其旒,异於生也。
先秦时代,人们认为,精气为魂,身形为魄。人若命至终毕,必是精气离形,而臣子罔极之至,犹望应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还复身中,故曰复。如君王死得不光彩,不适合名言,则言国殇。《国殇》之后是《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已明确说明这是礼魂作品。按照《诗经》和《楚辞》的习惯,一般先写主题表现,然后是作者的评价,所以《国殇》是祠怀王的场面,即招魂复魄,《礼魂》是屈原的议论,和《招魂》一起构成纪念楚怀王的组诗。
文章原载于《云梦学刊》2020年第2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名学文献整理及其思想流别研究”()研究成果。
【楚辞研究中心公众号第八十一期】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