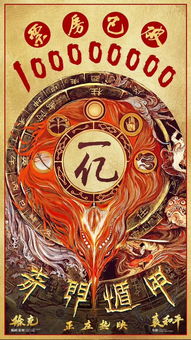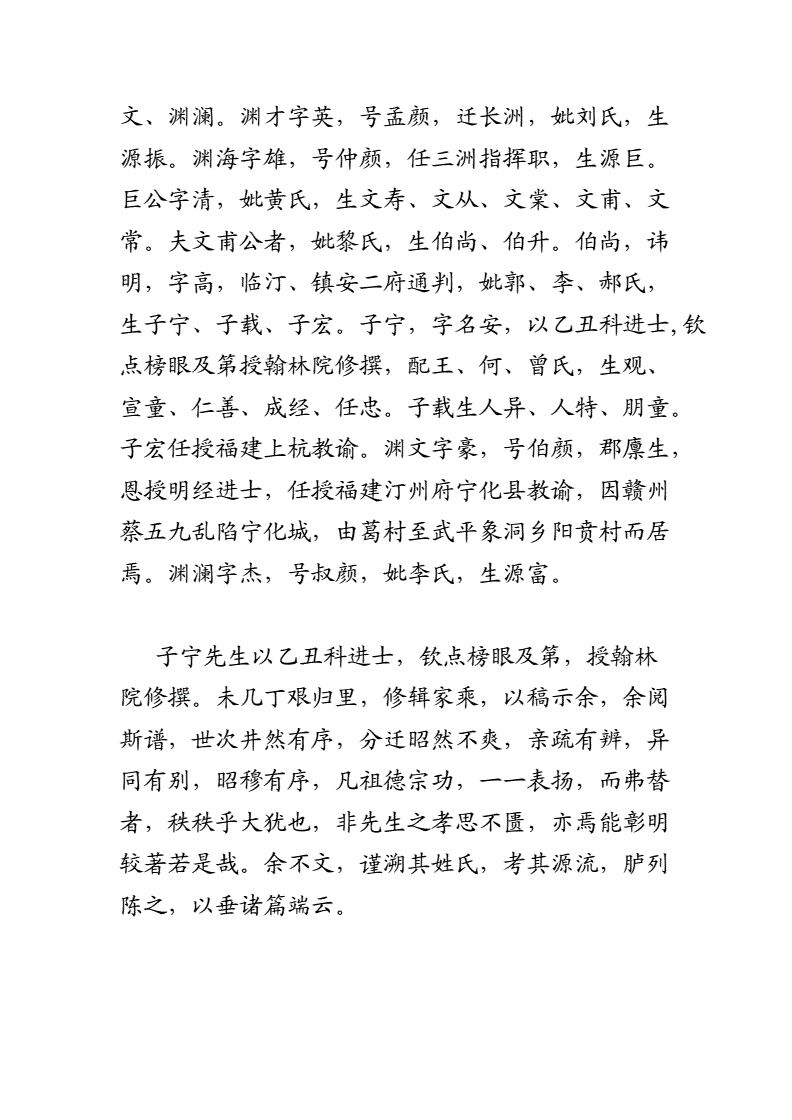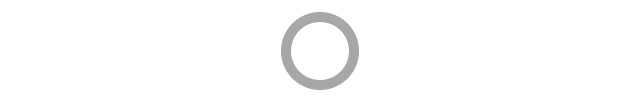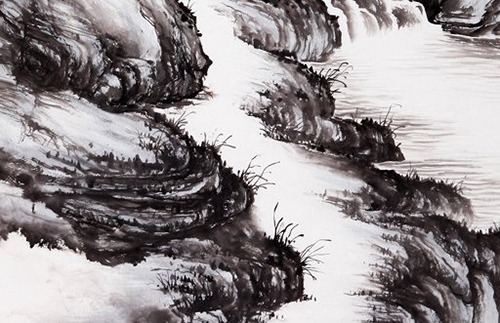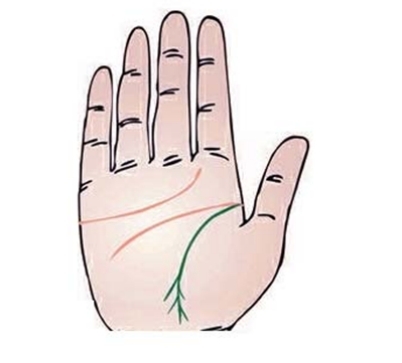小说:女子经常梦到恐怖死亡事件,为摆脱噩梦决定寻求筑梦师帮助
- 百科
- 3周前
- 365
她染着一头亮红色的、蓬松炸起的头发”对面沙发里端坐着一位与前者年龄相仿的女子,被称作祁妙的女子斜窝在沙发里,对面的女子下意识地看了看墙上,祁妙已经从提包里取出盒女士香烟,她这一问只是平定自己愈加焦躁的心绪,才算抬起眼皮望向对方,那个女人是被人从背后活活勒死的:眼珠子都快要从眼眶里掉出来,我身体没有任何毛病,我也知道噩梦是一种正常现象:

“已经是第三次了。”讲话的是个25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她染着一头亮红色的、蓬松炸起的头发,上穿高领黑色线衣,下穿灰蓝色喇叭牛仔裤,看起来就像一只贝蒂纳火鸡,“我实在受不了,才来到你们工作室,我知道只有你们才能帮我。”
“我们乐意为你服务。”对面沙发里端坐着一位与前者年龄相仿的女子,她穿一件水白色的职业套裙,瀑布般的乌发披在肩头,姿态谦恭,笑容亲和,“不过祁妙小姐,你能把情况介绍得更详细一些吗?”
被称作祁妙的女子斜窝在沙发里,一手撑着脑袋,一手抓着身侧的提包,似睁非睁的眼睛周围蒙着一层淡淡的青晕,——那不是眼影,而是一夜未眠的缘故。
“我想抽支烟,可以吗?”祁妙动了动睫毛。
对面的女子下意识地看了看墙上“禁止吸烟”的标牌,还未答话,祁妙已经从提包里取出盒女士香烟,抽出一支填进嘴里,尔后用打火机点燃。
“哦对了,我该怎么称呼你?”祁妙的话随着烟雾一起冒出来。
嗅到烟味,女子皱了皱眉毛,但仍旧保持优雅的微笑:“我叫尹昕,尹相杰的尹,吴昕的昕。”
很明显,祁妙并非真的关心对方的名氏,她这一问只是平定自己愈加焦躁的心绪。因为她在继续抽烟,直到把那支烟抽完,将烟屁股丢进不远处的垃圾桶,才算抬起眼皮望向对方。
“第一次是在半年多以前,那个女人是被人从背后活活勒死的,舌头吐出老长老长,眼珠子都快要从眼眶里掉出来。第二次是在大概三个月前,死的是个男的,被人绑上石头扔到湖里,等打捞上来的时候,尸体肿得像个沤烂的冬瓜。”说到这儿,祁妙稍稍挺了下身子,“第三次在一个星期前,是场车祸,死者是个男的,具体经过刚才都跟你讲了。”
尹昕一边执笔在纸上沙沙记录,一边问道:“这三个人,你都认识吗?”
祁妙摇摇头:“不认识。”
“噩梦发生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比如精神紧张,肢体感觉异常等等?”
“没有。”
“梦是人类潜意识的产物。之所以出现噩梦,除了心理因素外,还跟人的饮食习惯、睡眠姿势、所患疾病和服用的药物等有关。”尹昕慢慢搁下笔,“你平时喜欢看恐怖片吗?……”
“我身体没有任何毛病,我也知道噩梦是一种正常现象。”祁妙打断对方,“可问题是,那些噩梦全都在现实中发生了!”
尹昕略略吃了一惊。一般来说,噩梦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梦见十分恐怖的场景,第二种是被人以及动物、鬼怪追赶或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第三种是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可怕事情。但无论哪一种,都属于潜意识在客观世界和心理因素下的双重映射。
从科学角度讲,有的梦的确存在一定“预示性”。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不管多么精准无误的预测,都不难发现其跟现实之间发生的紧密逻辑。之前,尹昕也曾遇到过类似的病例,但梦主所述的对象,基本上是自己关系密切的亲戚朋友,像这种“预测”到陌生人的还是头一遭。
“中国这么大,非正常死亡的案子那么多,比如你说的这次车祸……”尹昕仔细斟酌着用词,尽量避免刺激到对方,“也许只是凑巧,又或者是你看到了车祸现场,然后附加给自己的心理暗示……”
“如果仅仅只是一次,那还勉强说得上‘凑巧’。”祁妙已经激动了,“可已经三次了,死的三个人也都在通宁,我连他们的尸体都亲眼见过,有这样凑巧的事吗?”
尹昕将冒着热气的杯子顺着茶几表面轻轻推过去:“喝点水,慢慢说。”
祁妙接过杯子喝了两口:“更痛苦的是,我随时随地在遭受他们的纠缠,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尹昕身上渐渐升起一股寒意:“你的意思是……”
“我能看到他们,那些死去的人。”说着,祁妙把杯子放下,抬起右手指着尹昕,“比如现在,车祸中死了那男的,他就惨兮兮地站在那儿,肠子流了出来,脑袋也变形了。”
尹昕注意到,讲这些话的时候,祁妙脸上没有特别过分的恐惧,也许半年多来她已经被折磨到几近麻木和崩溃。虽然不信鬼神,但尹昕还是下意识地转身看了看,除了一株盆栽植物和一个书架外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