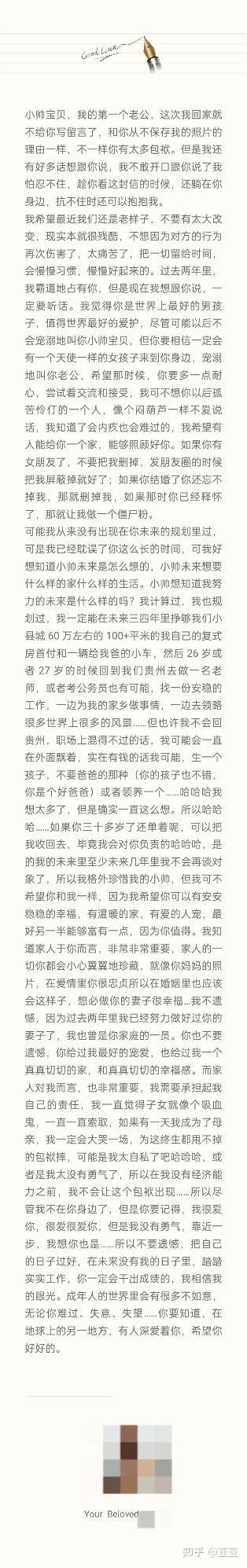短故事:她宁愿毁嗓也不为日本人唱戏,却最终嫁给了日本人?
- 百科
- 2周前
- 521

一、锦云社
本就是月朗星稀的光景,早前又下了一场雪,如今积雪反射着月光,把眼前的一切都染得宛若白昼。
晚霜提了提裙摆,从散落在地上的锣鼓家什上迈过去,戏台正中央的那把京胡已经崩断了弦,再也发不出丝毫声响。
她颤抖着,再往前一步,头顶凤冠上的珠子便哗啦啦地掉了下来,宛如落雨般,洒了一地。
她感觉自己的双腿突然没有了力气,心情也绝望到了极点,于是便委身坐在椅子上,透过洞开的雕花门窗看向前街。
前街的正中央,正生了一堆大火,全副武装的关东军正将尸体一具接一具地扔到火里焚化。
此刻,两名年轻士兵抬着的,正是她的老师傅,锦云社的老板沈胜沈七爷。他的躯体已冷,双拳却还紧紧握着,鲜血一滴滴地落在雪地里,如同一簇孤傲的梅朵。尸体被抛起来扔进大火之中的时候,激起的火星升腾到几米高处,又一点点地熄灭。
那一刻,晚霜本想冲出去跟那群关东军拼命的,可是最终还是忍住了,她知道纵然是拼上了自己这条微薄性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就在半个时辰以前,关东军荷枪实弹地闯入戏班时,沈七爷把她拉到一个角落里,交代她一件事情,他说务必要千方百计将那件事情转告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留洋去了国外的沈东岳。她还要留着这条命,完成师傅最后的托付。
虽然他对她说的那个秘密,仅仅只有三个字,每个字却重若千斤。
他说:“关马道。”
她不知道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只觉得那一定很重要,要不然师傅也不会在这生死关头,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还惦记着要让她把这个消息带出去。
他说:
“晚霜,一定要活着,无论多艰难都要活下来,记住了,关马道,关马道!”
那时的她都还被沈七爷蒙在鼓里,她一直以为三年前沈东岳真的去了国外,却不知道其实那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说法而已,彼时的沈东岳已成东北抗联的一名营长。
她更不会知道,有好多个夜晚,沈东岳带领士兵趁夜色躲开日本人的盘查,到锦云社搬运抗战物资的时候,都会在她的房间外面驻足良久。然而,为了保密,近在咫尺的他,甚至都不能与她见上一面。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晚霜捡起地上一块碎掉的镜片,微微正了正装,微微咳嗽了一声,第一次学着老生的腔调,看着窗外的熊熊大火,唱道:
“两狼山,杀胡儿……”
唱至情深处,不禁泪水涟涟。
此刻,却有一位尉官打扮的日本兵走到她的面前,顿了顿脚,深深地鞠了一躬,道:
“莫小姐,中佐有请,请跟我走吧。”
莫晚霜冷冷地看他一眼,双手小心翼翼地将头顶上早已破败不堪的凤冠摘下来,放在椅子上,然后披散着一头长发,直直地向着门外走去。
半里以外的关东军司令部里,司令长官小泽一郎早已为她准备好了住房,并且摆上了酒菜,点头哈腰地将她请进房中,笑道:
“莫小姐肯定受惊了吧,鄙人不才,略备小菜,为莫小姐压惊。”
“你怎么不把我一起杀了?”莫晚霜并不领他的情,恶狠狠地看着他怒斥道。
“呵呵,莫小姐可是整个满洲国最有名的花旦了,杀了不太可惜了吗?小泽今天把莫小姐请到这里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也是爱好和推崇艺术的,如果莫小姐愿意的话,等到战争结束了,我可以把莫小姐送到日本,到那时,你就可以把京剧艺术发扬光大了。”
莫晚霜不再说话,她知道这种情况下多说无益。
自从十年前,她在各地的军阀混战中辗转流浪,最后被沈七爷收入门下以后,她就刻苦练习京戏,整整十年时间,她由一名小小的学徒,漫漫地成长为锦云社的当家花旦,挑起了大梁的同时也使得锦云社渐渐在行内出了名,如今却毁于一旦。这里面的艰辛和不甘,唯有狼子野心的日本人又怎么会懂,他们怎么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
“其实鄙人一向都是欣赏莫小姐,爱慕莫小姐的。”
说着话,小泽一郎竞还压了压嗓子,唱起了一段京戏,扭捏作态,东施效颦之嘴脸跃然眼前。
莫晚霜心生厌恶,不禁将脸转向了一边。见她冷漠,小泽自知无趣,脸上不禁也尴尬起来,旋即换了一种严厉的语气骂道:
“实话告诉你吧,进了关东军的司令部,你唱也得唱不唱也得唱!我的士兵千里征战,异常辛苦,以后还指望用莫小姐的戏来劳军呢。”
说到此,他顿一下,接着又想到什么似的说道:“对了,三日后,关东厅的山木长官要来这里视察,你好好休息几日,到时必须登台。”
说着话,不等莫晚霜回答,他便猛地甩门出去了。
莫晚霜向前一步,轻轻地坐在床边,脚下的火盆里明火已经熄灭,却余下一盆红彤彤的火炭,那一刻莫晚霜突然就想起沈东岳来了。
她记得他从小便不爱学戏,出生在名伶世家的他,总是凭借自己的号召力,带着当地的一群顽皮孩子,到处惹是生非。有一次,不知天高地厚的他还打了一位日本领事的孩子,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沈七爷硬是拿出了半生的积蓄,赔给了那个日本人。
那一天,沈七爷罚他扎马步,膝盖下面点着青香,虽然明显已经极其疲惫,表情也异常痛苦,可是他依旧坚持着,因为倘若放松警惕微微弯了一下腿,燃烧着的青香就会烫到他的皮肉。莫晚霜实在看不下去,便跑去跪求师傅,结果换来的结果却是两个人一起受罚。
那一次,虽然膝盖被烫起了一串燎泡,但她还是很高兴,她傻傻地认为,无论多大的考验,只要她愿意替他分担,他的痛苦也许就能减轻一点。
她想,那时的沈东岳胸中便满怀国仇家恨,而如今自己却沦落到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苟延残喘的地步,着实令人汗颜。那一刻,她本来是想一头撞死在墙上的,可是最终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她的心中一直想着沈东岳,仿佛她与他之间还有一个未完的约定。
可是,她又不愿意为日本人唱戏。
他们杀了沈七爷,抢了戏园,甚至连妇女孩子都不放过,给这些禽兽不如的人唱戏,她宁愿死。
想到这里,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她突然弓身捡起火盆里一块烧透了的木炭,扔进口中吞了下去。
滚烫的火炭卡在她的喉咙中,炽热无比,疼痛难忍的她却一直紧闭双唇,不愿将它吐出来。她的身体蜷缩成一团,不停地在冰冷的地上翻滚,她的体内仿佛正往外涌动着一股岩浆,而身下却是寒冷的地砖,那种感觉,仿如炼狱,又如同涅槃。
她颤抖着,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她说:
“我绝不唱,绝不……”
最后一个字卡在喉咙里,如同撕裂的锦缎。
她,失了声。
二、花落败
莫晚霜再也不能唱戏了,喉咙被严重灼伤的她,甚至再也说不出一句话,那时她本以为小泽一郎见她无利可图就会放了她的,可是她锚了,她忘了自己除了嗓音,还有美色。
得知莫晚霜吞炭以后,小泽一郎大动肝火,重责了守门的士兵之后,又请来当地有名的中医为莫晚霜调理护嗓,可是那块炭火几乎烧穿了她的喉咙,纵然是华佗再世,也是束手无策。
身为中佐的小泽何曾受过这般戏耍,于是难免恼羞成怒,夺过士兵手中的长抢,用枪拖对准莫晚霜狠狠就是一砸。
莫晚霜再次醒来时已入夜,额角的鲜血已经结了痂,伸手一碰便有钻心的疼痛传来,床铺的对面有一面
巨大的穿衣镜,镜子里面的女子形容憔悴,衣衫凌乱,而镜子的旁边,小泽正在整理着自己的军装。那一刻,莫晚霜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她大叫一声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向着不远处的小泽冲去,可是才跑到他的身边,他却忽然转过脸来,抬腿便是一脚。
一阵乱响过后,莫晚霜已经牢牢地跌坐在了地上。
小泽一郎脸上泛开阴冷的笑意,缓缓地走到莫晚霜的面前,用一根手指挑起她的下巴,讥讽道:
“莫小姐你可真是傻呀,以前鄙人尊敬你,是因为你是整个满洲国乃至整个支那有名的旦角,而如今,你自毁前程,能为皇军效劳的,恐怕也只有身体了吧。”
说着话,他猛地一甩手,莫晚霜的额头便重重地磕在了床角,她听见他对自己说:
“莫小姐如果愿意,以后可是跟在我左右专门伺候那些需要打点的上层军官,如果不愿意,那我只有把你送到军营里面去了,那里的士兵可是又脏又臭的。”
夜空中的月亮缺了半边,孤零零地挂在藏蓝色的天空中,看起来是如此无依无靠。莫晚霜清楚而绝望地知道,凭她一己之力,根本就无法跟关东军作对,他们已在当地横行多年,爪牙遍布东三省,就连抗联为了躲避他们的追剿也不得不暂时躲进了深山老林之中,更何况她一名小小的戏子。
也正是因为怀疑锦云社与抗联有染,暗中曾偷偷收治从战场上乔装撤下的抗联伤兵,并且多次为抗联提供军需物资,所以才会遭到了灭门之灾。
后来,她便从了小泽一郎,时常伴在他的左右接待那些前来视察的日本政要,她陪他们吃饭,喝酒,跳舞,甚至侍寝,却从未开口说过半个字。
周围的中国人对她褒贬不一,有的说她有骨气,宁愿毁了嗓子也不为日本人唱戏,也有人说她是在做戏,最终还是贪恋日本人给的荣华富贵,要不然,怎么会整日跟在日本人的身边。他们甚至说,自古戏子无情,女儿胸中无家国!
面对众人的非议,莫晚霜尽量不去听,也不去想,她就像尊表情僵硬的精美雕塑一般,坐在一群日本男人中间,慢慢地淡了光华。
而她心中,始终牢记着那三个字,也始终牢记着从小一起陪她长大的沈东岳。
三、再相见
再次见到沈东岳已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那时的莫晚霜已经把名字改成了莫奈,取无可奈何之意,她固执地认为自己已不配再叫从前那个名字。
彼时的她被一位名叫龟岛一雄的日本少佐看中,托了关系,千方百计地从小泽一朗的手中要了过去,娶为了妻子,结束了灯红酒绿的交际生涯。
虽然龟岛一雄对她百依百顺,千般讨好,并一再发誓说不在乎她的过去,只要她一心一意地对他好。但她还是对这个日本男人毫无感情,她只是静静地陪在他的身边,尽量做好一个妻子该做的一切。
那一次,她陪龟岛到教堂里做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了一身灰色长衫,帽檐儿压得很低的沈东岳。龟岛一雄指挥着关东军的一个联队,每次执行任务杀了中国人之后,都会到那所教堂里面去祈祷,乞求上帝的原谅。
莫晚霜虽然觉得他这种假惺惺的做法很恶心,但每次也都会跟随前往,她想,现在的沈东岳肯定已经得知了锦云社惨遭灭门的噩耗,也许他已经回来了,说不定就能在某个街头遇到他呢。
她虽看见了他,却不敢相认,只远远地看着,四目交会之时,她看见他的眼中充满了怜悯和怨恨。是啊,他一定是从坊间听说她投靠了日本人,曾经心爱的女子明珠暗投,他又怎能不恨。
于是,她便慌忙低下头来,不敢再去看他的眼睛。
那几日,莫晚霜跟着龟岛到哪儿,沈东岳便尾随到哪儿。她想,也许下一秒,他就会从怀里掏出枪来把自己给杀了,如若真是那样便倒好了。
可是他却没有。
光怪陆离的歌舞厅里,她在龟岛的介绍下伸出戴了黑纱手套的右手跟那几位日本军火商人打招呼,沈东岳就坐在一旁的沙发里低头品着咖啡。好不容易托了去洗手间的由头,给沈东岳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他跟上来。
而他却仿佛没有看见似的将脸背向了一边,那一刻,她突然有些绝望,她觉得他肯定恨透了自己,她怕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完成师傅交给她的那个任务。所以当她从洗手间走出来,迎面撞上面无表情的沈东岳时,还是禁不住有些激动。
她想对他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却像团棉花塞在喉咙里面,怎么也发不出来。
她深情地望着他,眼中噙满了泪水,而他却是一副冷冷的表情,许久才从嘴角挤出一句话:
“晚霜,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不远处的龟岛正在向这边观望,也许是因为觉得她去的时间太长了,难免有些担心,虽然是在日本人控制的地界,但这里毕竟是中国,莫晚霜又曾是名人,现在成了中国人眼中的“汉奸”,他不得不为她的安危着想,毕竟他是真心喜欢她。
看着龟岛一步步地向这边走来,纵然心中藏了万语千言,那一刻的莫晚霜也只能上前一步,匆忙把一方锦帕塞在了沈东岳的手中。手帕上,是她咬破自己的手指,写就的三个血字——关马道。
与他肩膝交锚的刹那,莫晚霜突然很想放声大哭,可却还是对着向这边走来的龟岛露出了微笑。
当龟岛赶上前来,在她的额头印下那轻轻一吻的时候,她在洗手间的镜子里面清晰地看见沈东岳愣了一下,然后压了压帽檐儿,匆忙走了出去。那一刻,她明显在他的动作里看到了慌乱。
她望着镜子里他那快速离去的背影,在心中喃喃道:
“亲爱的沈东岳,还记得当年我唱那出《公主出嫁》时的情形吗,那出沈师傅编的戏,我一共唱了不下百场。我身披锦袍,头戴凤冠,每唱一句,心里想着的都是正在嫁给你。”
彼时,戏台上的她是万人追捧的名角,就算饰演的人物,也是高高在上的公主,而此刻,她却只是一具身陷藩篱的落拓女子,一朵早已凋零的花。
四、关马道
得知沈东岳带领的队伍在关马道遭受日本人的伏击,是在第三天头晌。
一夜未归的龟岛告诉她,昨天晚上关东军在一个叫关马道的地方成功地伏击了前来搬运食盐的抗联士兵,除三人逃脱以外,其余全部歼灭。
直到那时,莫晚霜才知道,日本人为了有效地打击抗联的有生力量,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切断了进山的粮食和食盐通道,也正是因为如此,抗联才派人偷偷地潜八日占区,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联络点,偷偷地为部队提供粮食和食盐。
锦云社也就是在那时候成为抗联的秘密联络点的,当时沈七爷凭借自己在当地的地位和影响,积极鼓动一大批爱国人士为抗联筹措战略物资,后来这个秘密被关东军探知,才一举捣毁了锦云社。
那时,沈七爷正秘密准备了一批食盐准备等沈东岳下次来的时候运进山支援抗战,可是还没来得及出手,自己就先遭不测。
而所谓的关马道,就是他们秘密囤积食盐的地点。
日本人本来以后那些战略物资都藏在锦云社里,可是等他们杀害了沈七爷之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后来,他们本来已经打算放弃了,偏巧不巧,昨夜一位醉了酒的日本军官在关马道酒楼闹事,几个当地人看不过去,便用一条麻袋套了他的头,毒打了一顿。
日本警备厅的人自然不愿善罢甘休,于是便派了一小队人马包围了整个关马道,结果正巧赶上了已把食盐装车,准备混出城去的沈东岳。
经过一夜的激战,龟岛明显已经累了,说完话,便让莫晚霜帮自己脱下衣服,倒头便睡。莫晚霜愣在床边,足足愣了半炷香的光景,想到那日自己把锦帕塞给沈东岳时的情形,眼泪禁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扑簌簌落下。
窗外的小广场上,一群士兵正在把昨晚击毙的抗联士兵的尸体从军车上抬下来,在地上一字排开,一位穿着燕尾服,留着西洋头的日本记者正在逐一为死者拍照。
莫晚霜轻轻地擦一擦眼泪,向前一步,踱到窗前,踮起脚,试图看清那群死者当中有没有沈东岳。其实那时的她心中早就盘算好了,如果他们真的杀死了沈东岳,她便用剪刀刺死熟睡中的龟岛,然后点燃屋子与他同归于尽。
可是,任凭他如何张望,也只能勉强看得见一张张血肉模糊的脸,她请清楚楚地记着沈东岳的右边手腕上是有一个小小的黑痣的,纵然是他的脸已经分不清,她也能就此认出他来,就算连他的右臂也被打飞了,他的双腿也还是在的吧,他的膝盖上有好多香疤,那便不会错了。
这样想着,好不容易等到众人散去,她才小心翼翼地从房内走出去。
军营里的士兵大都是认得她的,平日里对她也都无任何防备,有些从其他战区新调来的士兵,甚至一直都还以为她是个日本人,所以见她从长官的房间里走出来,直直朝着那一排尸体走去,也都没有阻拦,顶多是在她面前立正站好,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
莫晚霜离尸体越来越近,她的心中虽然迫不及待地想要看清死者当中到底有没有那个自己心爱的男子,可是越到跟前,脚步却越发慢了下来,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了自己的心尖。
她怕那群死者当中果真就有沈东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恐怕今生今世,来生来世,她都不能原谅自己了。
七八名死者当中,有六个明显不是沈东岳。
剩下的两个身形相似的,其中一个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另一个的脸已经被打烂了。她跪在地上,颤巍巍地伸出手去,闭着眼睛拉开他手腕上的衣服,然后猛地睁开眼睛,好在,那名死者的手腕上并未有痣。
她想笑又不敢笑,只能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心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可是刚刚想到这里,胸中却泛起一阵恶心,连连干呕了几声。
“浑蛋,怎么能让莫奈小姐看这种场面,你们不知道他是我的妻子吗?”
身后传来了龟岛教训士兵的声音,在甩了那名卫兵几个嘴巴子之后,他穿着木屐,嗒嗒嗒地跑到莫晚霜的身边,一把将她搂入怀中安慰道:
“莫奈不怕,死人有什么好怕的,习惯了就好了,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也曾忍不住呕吐来着,习惯便好了。”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对身后的士兵打了个手势,让他们把尸体运走。
此时,莫晚霜却又接连呕吐了几次,虽然腹中异常难受,但莫晚霜的心里却是欢喜的。
沈东岳没有死,沈东岳没有死,我没有害了他。
这是她心中唯一的一个想法。
五、家国恨
莫晚霜断断续续接连呕吐了几天,一开始龟岛以为她是因为看到了恶心的画面导致的正常反应,后来见她已经吐个不止,才请来了一位中医。
老中医在为莫晚霜把过脉之后,居然一脸笑意地告诉龟岛说莫晚霜有喜了。
虽然龟岛异常兴奋地向老中医道了谢,并大方地赠给他十块光洋,但这个消息对莫晚霜来说,却无异于天公在她的眉目之间打了一个霹雳。
她,居然怀上了日本人的种。
那几日,她茶饭不思,脑海中成日浮现出以前尚与沈东岳生活在一起时的画面——年仅十岁的她,端着一只破碗,轻轻地掀开锦云社的门帘,怯生生地乞求道:“给点吃的吧。”
尚在中年的沈七爷看她可怜,给她用包裹包了些许干粮,并且替她拿了几件徒弟们穿旧了的衣裳,本要打发她离开的时候,却有一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小男孩,从背后拉了拉沈七爷的衣角,瞪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企求道:
“爹,她那么可怜,就让她留在这里吧,日本人的东洋马会把她踩死的。”她想起,小时候的自己因为练不好基本功,经常会被严厉的师傅抽手心,是他偷偷地溜进她的房间,钻到她的被窝里,将一小瓷瓶红花油递到她微微发疼的手中,说:
“晚霜,你用这个,以前我不听话,爹用竹条打我的时候,娘就是偷偷用它为我治伤的,可管用了。”
她想起这些事情,又联想到他现在的生死不明,脸上不禁泛起一抹凄惨笑意。
她不知道沈东岳去了哪里,不知道此生还有没有机会再与他见面,如果还能相见,他会不会以为是自己出卖了她,毕竟所有的事情都赶得那么巧。
就算他信她,不怨她,她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脸再重新回到他身边。毕竟,她的肚子里面已经有了别人的孩子,而且还是个日本人的孩子。
这样想着,她胸中突然打定了一个主意,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莫晚霜跳入那口结了一层薄冰的水缸是在半个月之后,从总部开会回来的龟岛,将她从水缸里抱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冻得脸色发青,整个人几乎缩成了一个疙瘩。
后来,她整整腹痛了十多天,那种疼痛,就像是有个小人钻进了她的肚子里,拿刀子一下下地剜她的肉。
后来,她的下身流出一团模糊的血肉。脸上毫无血色的她在那一刻居然笑了起来,她的笑就像是一朵雪地里打了蔫的莲花,一点点地凋零在东北平原黑色的大地里。
她努力地张开嘴巴,用一种异常难听刺耳的声音喃喃说道:
“沈东岳,晚霜,晚霜,终于可以干干净净地见你了。”
好在那一次,龟岛并没有责怪她,那几日,他抛开一切公务,整日陪在她的身边,就是担心她会再次做出傻事。
他说:“莫奈,我知道你恨日本人,也恨我。你恨我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你恨我们占领你们的土地,可是,我也是情非得以,军令难违。我不知道这场该死的战征是不是把我变成了一个魔鬼。我只知道我是深深爱着你的,这,这是自从我进入中国以来,唯一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每次,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
可是,无论他如何劝说,如何安慰,莫晚霜的脸上却只是挂着让人心生寒意的微笑。她看见,春天来了,东北的黑土地上开满了黄色的迎春花,她看见自己穿着漂亮的七彩霞帔,戴着金光闪闪的凤冠盔头,唱一出只有相守没有别离的温柔戏。
六、姻缘诀
最后一次遇见沈东岳是在来年冬天。
那时,莫晚霜的身体已经渐渐好转,为了让她忘掉以前那些悲伤的事情,龟岛时常带她出入那些高档的娱乐场所,歌厅、影院、日本人设的武道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那晚,莫晚霜突然想要去看一眼早已不复存在的锦云社。于是,龟岛便命令司机将本来要去向影院的汽车在第一个道口拐了一个弯,直直地向着隔了几条街的锦云社驶去。
锦云社还是当初的格局,不过却早已不复当年的辉煌,四处散落着家具桌椅,房梁之上结满了蛛丝,蛛丝上又结满了灰尘,稍一碰触就会扑簌簌地掉下来。
她知道,如果沈东岳活着他今晚一定会回来,因为今日是师傅的忌日。
龟岛以为这里不会再有人来,便独自陪她进去了。可是走进后院,才恍惚看见,正堂之中似乎有火光闪烁。他伸手将她隔在身后,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
可刚踏出没几步,便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整个身体便轰然倒地。再看时,一身长袍的沈东岳正从那间闪着火光的房间里面走出来。
他面无表情地朝着莫晚霜走过来,经过龟岛身边的时候,双腿却被龟岛紧紧地抱住。龟岛一边抱住他的腿,一边用一口并不怎么熟练的中国话对着莫晚霜喊道:
“跑,快跑。”
可是,她又怎么会跑呢,她这一生想着的便是千方百计地重新回到沈东岳的身边,无论等待她的是天堂还是地狱,她都已毫不在乎。
砰!
一直疯狂叫嚣着的龟岛终于安静下来,一滴清泪沿着莫晚霜的面颊缓缓地落下来。
她抬起头来,笑着看着在自己面前缓缓举起手枪的沈东岳。
其实那一刻,她本来可以向他解释一切的,可是最终还是放弃了,她觉得在他的印象中,她的声音一向都是那么动听,那么美,她不想,再让这仅存的美好破碎。
她听见他说:
“晚霜,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昧着良心背叛锦云社,背叛民族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师傅的忌日,死在他灵位的面前?”
莫晚霜只是笑,只是笑,她不再去争,也不再去求。
沈东岳伸出手来覆在她的脸上,试图让她闭上双眼,从而减轻她的恐惧,可是她却笑笑地,将脸贴在他温热的手心,忘情地摩挲着。
她抬起头来,将眉心对准枪口,深情地望着他,她在心中默默地对他说:
“亲爱的沈东岳,我已无法爱你了,也不能再对你唱,我能做的只有为你死。请原谅,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将一切隐瞒,因为我知道,有些时候,恨要比爱,痛快得多。”
砰的一声枪响,震落大片仿佛隔世般久远的尘埃,好大一场姻缘戏,落幕在人去楼空的大舞台。
上一篇
酉时出生的属虎人命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