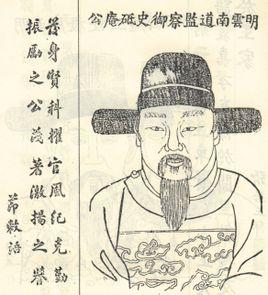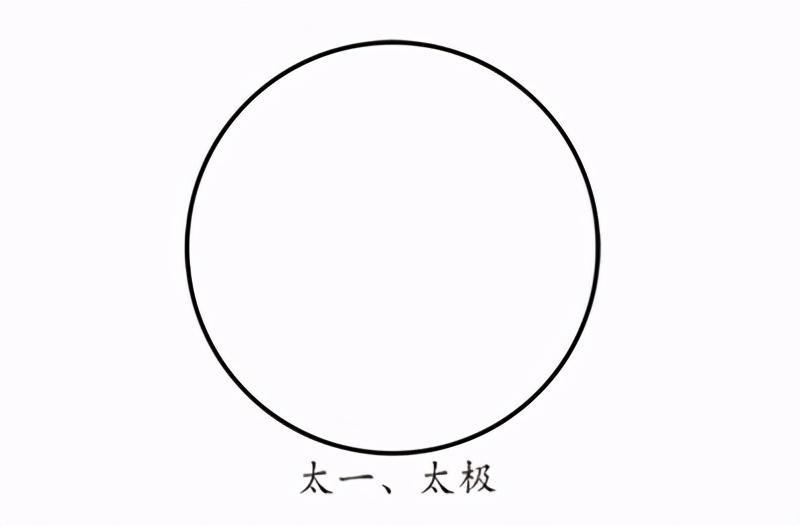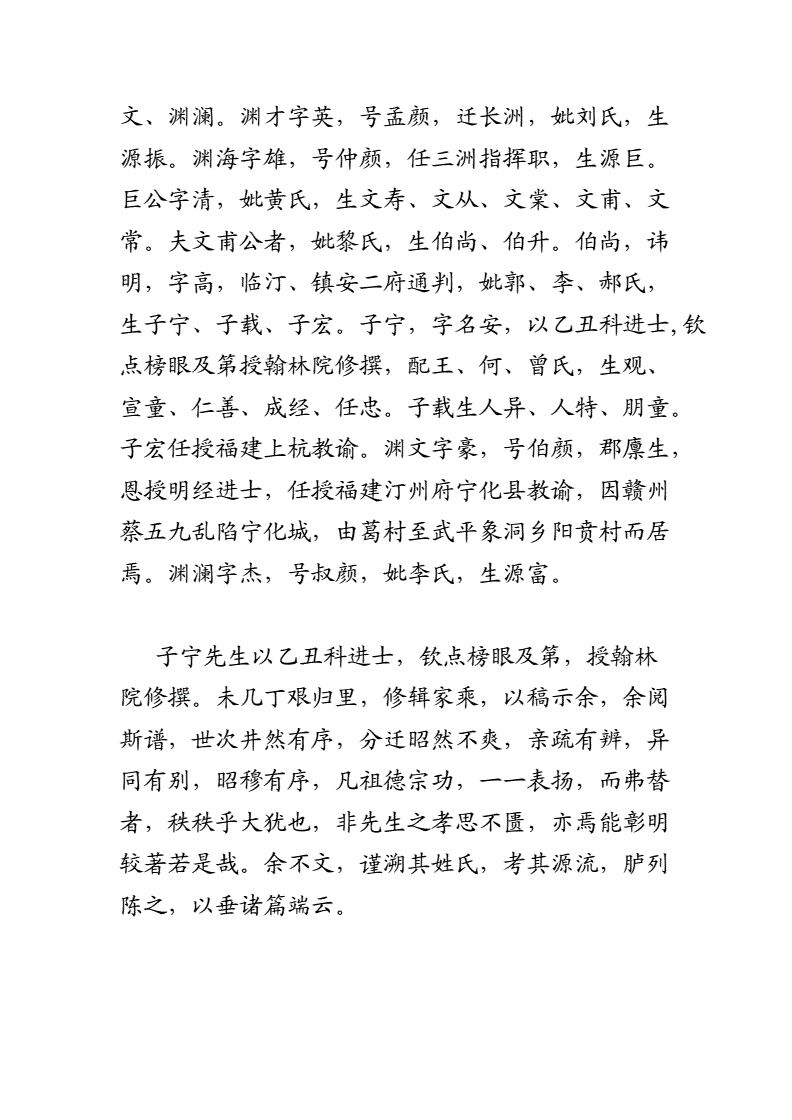《易经》心解——与文王面对面
- 百科
- 2周前
- 799
三千多年前的羑里,有一条河由城北转而东流。旷野之上,屋舍散落若干。一位老人,幽禁其中。东篱无菊可采,西窗无雪可望。唯有一束蓍草,伴随着鸡鸣狗吠,还有那时隐时现的漫天星斗。
命理师念鲜的微信:nianxiangege这位老人,不停地分着手里的蓍草,拿起,放下,合拢,再分开……不计日夜,时空也仿佛为之融化。斗转星移,终于有一天,他推开所有的蓍草,走出屋外,望着那奔流不止的河水和隐约的星斗,仰天大笑:
易者,不易耶?
这位老人,就是演绎出八八六十四卦的姬昌,被后人称为周文王。
大约五百多年后,乔达摩·悉达多,印度一位舍弃王位的智者。六年苦行后枯瘦如柴的他,喝下牧女供上的一碗牛奶之后,端坐在菩提树下。虽然茂密的枝叶遮盖住了天空,遮住了闪烁的星辰,可他内心的星空却彻底地粉碎了: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无踪无影可觅,却又无处不在。小到一粒微尘,而其中却遍满三千大千世界。这种“能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贯穿于每一颗心,抑或一粒尘埃,只是自知或不知而已。他感叹着:奇哉 ! 奇哉 !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能德相,只因妄想而不能证得。
几乎是同时,东方的中国,有一位夫子,伫立大河之畔,面对这滚滚东流的河水,唱和道:“逝者如斯夫”;道之哉,“百姓日用而不知”。
还有一位老者,骑着青牛,出关西去,口里喃喃自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分明是用另外一种形式道出了文王演绎八卦的用意和宇宙运行的真理。他的身后,追随着关伊子、庄子、魏伯阳、葛洪、吕洞宾、张伯端、全真七子……花样迭出,却万法归一,可谓性命本不离,道易无二致。
三千多年后的今天,我再一次叩开《易经》之门,来到了这个高远而深邃的空间里,拜坐在老人面前。我看到了他闪烁着无尽光辉,以及身后那些无穷无尽的脚印,大大小小,若有若无,好似一个个太极图,延伸到现在,通向未来,把我和他连接在了一起。这些脚印中,有姜子牙、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有京房、郑玄、王弼的;有周敦颐、邵康节、二程、张载、朱熹的……如繁星般徜徉在浩瀚的太虚,却遵循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轨迹,如银河系的星云图,抑或是太极的模样。这些“模样”,绽放着七彩的光芒,光芒里闪射者一行行若隐若现的字:
“神无方,易无体也”;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时空有分段,大道无古今。古今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本来的实义从未中断,也未曾消失,绵延不尽。到了南宋的大儒陆象山这里,一声长叹,抒发出了“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大和之声。明朝的王阳明,这个前世的和尚对心的阐释又是多么的潇洒:先生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宋明理学两派,亦如禅宗的顿渐,异曲同工,相互辉映。若换成夫子,或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若无通,儒则无法达到天人合一,道则如何法诸自然,释家也更难桶底脱落,明心见性。而若有通,则非寂然不动而不能至。儒之至诚无息,道之丹鼎吐纳,释之四禅八定,皆入定而通之路径。故佛家语言,定能生慧。此慧之生,貌似感通而外得,实乃对境生心。
生的什么心?夫子说:圣人作易,是为了让众生明白顺天道养性命的道理。所以立天之道称为阴与阳;立地之道,称为柔与刚;立人之道,称为仁与义。曾子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北宋的张载则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如此诸心,不外乎“利他”二字,就是菩萨行!
发了这样的心,发了这样的愿,再付出相应的努力,就是圣人作易的本义。法由人兴,法为人用。民之所受,民之所感,无论吉凶祸福,究其实质还是自作自受,天理昭昭,因果循环,怨不得英雄,怪不得凡夫。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因果史。要紧的是,把因果之理,天地之道告诉众生,让其明白:生死烦恼,穷通贵贱,无不由自心造作而成。如此,则人人尊天道,循因果,如孔子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亦即文佛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
于是,我反观自己,犹如一粒粟米,在广袤无尽的土壤里扎根,正试图体味着易的真谛和文王的本意;试图本着象、数的基础而阐述义理;竭力地把因果返归于易,把至善至德还归于易,把儒释道的相共相通返还于易,以期圣人之道得以大观,天下百姓得之而趋大同。我再看那文王,看那《周易》,看那八八六十四卦,我看到了:
佛法是心法。以心法去看《易经》,不过多了一个角度而已。多一个角度,就多一分精彩。其实,的精彩在于没有角度,没有精彩。佛法中有易理,易理中有佛法,遍融入故。没有褒贬与扶抑;若见不平,心不等故。
━ 者,阳也;至诚之心,没有穷尽与边畔,无处不在,又无影无形;此为信门入;– –者,阴也;虚而空,空而明,念起念落心明了;此则理门开。理事并行,皆通达故。– –之一分二,乃一之二,合之则为二之一也。 – –之前段,前念也;之后段,后念也。前念已过,后念之未生,中间那个是什么!没有前后,中亦不显;若无中间,前后也不存。是故《心经》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也好, – –也罢,不过一个符号而已。道虽不在文字,然不离文字;法由人兴故。
神无方,易无体,就是心法,无所得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万物都从空中生,诸佛皆自法身出故。
六十四卦,多么的伟大和奇妙啊,三百八十四爻,无穷无尽的变化,如同那绚丽夺目的菩提树枝枝叶叶,无论它繁茂得如何铺天盖地,也遮盖不住星辰之光;无论多多少少个智慧的足迹纷沓而来,前赴后继,也都离不开太极这个根;无论古今内外多少贤圣穷辞辨义,无非是倡导循天道尽人事而已。《易经》之道,就是君子道,就是圣人心,就是菩萨行。所以禅宗六祖言:“心量广大,周边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六祖之心,即文王之心,亦即天地之心,易之心。一切即一,即万物返阴阳,阴阳归太极;太极之中自含万物。一即一切,亦即万物皆由太极生,万法皆从自性出之理。故佛家曰:大海自能生波浪,波浪灭后还成水。
环顾苍茫天地,风云呼吸,雨雪飘摇;云蒸霞蔚,电闪雷鸣;山高仰止,江河奔流,日月交替,何曾停息。万物鸟兽,草木百谷,春生夏长,秋敛冬藏……一切的往来都是那么的自然,无一丝一毫相互妨碍。一旦有了人,人有了心,心有了分别,有了私我,有了欲望,这天地之气便开始随着人心而变化和动荡。而《易经》八八六十四卦的用意,无非是令人心安慧明,尊顺天地之道而已。归根结底,易或不易,还是一个“心”字。故蕅益大师言:“六十四卦大象传,皆是约观心释。所谓无有一事一物而不会归于即心自性也。本由法性不息,所以天行常健。今法天行之健而自强不息,则以修合性矣。”
老人笑了。
是以为序。
月光童子于惠灵顿
丙申年甲午月丁亥日(2016 年 7 月 4 日)丁未时
后 记
惠灵顿是新西兰的首都,也是我的福地。
我的《易经——中国古代大数据》一书的起源就是在这里,当时写的多是随笔,以期推重因果之道在术数中的作用。回国后,我几经修改,反复推敲。终于,书稿的前一半内容后得以成书出版;后一半因为涉及具体的占卜内容和实践经验,所以割舍掉了。眼下这一本书,前半部分在国内写了九个多月;后面一半在惠灵顿居然一个月就写完了,有如神助。每当我思路走到尽头,便站起身眺望远处的大海;或者烧壶水,泡泡茶;或者焚香,诵一部经;乃至于上个洗手间等等,很快便思如泉涌,问题就解决了。古人读书云枕上、厕上、马上,我思考问题则多是厕上、枕上、坐上。所谓“坐上”是因为我每天都坚持禅坐一定时间,本来是为净心的,结果满脑子都是爻辞、卦辞。许多解释,都是来自坐上的灵感,刹那间的事。这只能说是往昔的种子发芽成熟。譬如蒙卦之“纳妇吉”的解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发挥,对“归妹”的不同理解,困卦的演绎,井卦的发挥,明夷卦的新论,丰卦的“斗”、“蔀”,既济卦的独特理解等等,许许多多的新思路,如闪电不期而至,让我体会到了易理的博大精深和浸润其中无穷尽的乐趣。
就我个人而言,大致把研究《易经》的人分为这样几类:一是以孔子、子夏、郑玄、王弼、程颐、朱熹等人为代表的义理派,二是以象数为重点的焦赣、京房、虞翻、邵雍、来知德、尚秉和等人的象数派,三是李鼎祚、王国维、顾颉刚、闻一多、郭沫若、高亨等人的考据派。前两派秉承卦象、卦数与义理三位一体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天地人由道而一体化三的阐释,把《易经》尊崇到中国文化源头的高度。而后者的考据派,我个人认为闻一多成就。郭沫若等则多偏重于对字词的考证以及把一些历史事件与《易经》相关联起来,更倾向于《易经》反映的是当时的历史。除此之外,还有李镜池等人,独辟蹊径,把一部《易经》六十四卦“世俗化”,认为仅仅是反映了当时不同人的生活状态,为当时不同阶层的人士占卜的一本“汇录”而已。譬如李镜池先生对于《易经》的“孚”字,几乎都解释为“俘虏”,彻底抛弃了“诚信”的意义,是非常不恰当的。还有人认为遁卦是猪的逃遁,否卦是淫奔妇的浪史,丰卦说的是女神,井卦说的是猎野兽,乃至于恒卦是女猎人以及她的夫子,乃《易经》的原创者……实际上是把《易经》的研究导向世俗化,当然也是对《易经》的贬损和对先贤思想的否定。还有人认为,帛书《易经》才是更原始的,孔子不过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对《易经》进行了阐释而已,未必符合原意。诸如此类的观点,虽然别具一格,但也未免难免离题太远。
我是这样来看《易经》的:
帛书版《易经》未必是更早更原始的,卦序的排列乃至于文字也未必是准确的。即使如此,也是漏洞百出,周文王才加以演绎和改进。佛说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知道,修行人讲闭关而克期求证,或三月,或三年,长短不一,就是为了制心一处而求开悟。而文王于《易经》,一心一处用了七年啊。后天八八六十四卦之所以流传到现在并且为社会接受,必然有它的因缘,有它的合理性。古人有古人的角度,今人有今人的视野。不管怎么样注释、解释,只要对自己的身心有益,对读者的身心有益,我认为就是成功的。当然,种种见解,都要以《易经》的象、理、数为基础去阐释,不能胡乱猜测,误人子弟。卦辞、彖辞、象辞、爻辞,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有后世大量的占卜实践,以极其高的准确性可以反证《易经》言之不虚;所以说研究者必须精通占卜之术,否则仅仅解释字词是难以入其堂室的。譬如汉代大儒郑玄就非常精通卦象与卦数,他十七岁的时候就根据忽然刮起的大风,而推算出某地在某时有大火,并且向县衙门报告,以作准备。到了某一天,果然如郑玄预测那样发生大火。由于准备得早,而没有造成大的损害。如王弼,有“人天感应”之功,仅仅活了二十四岁,却被后世道家尊为“真人”。他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寂然无体”四字,就是 “十翼”中“寂然不动”和“神无方,易无体”的概括;所以他既秉持了孔子的理念,又直接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与《易经》本义相互辉映,对后世的理学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古代先贤无论怎么演绎,甚至看起来某些地方有些矛盾,但细细分析再看,必有内在的合理性;因为他们大处能够从阴阳正反两个方面去分析,对立而求统一,统一而不离对立;小处可以精通术数预测,并以此而法天地之道而尽人事,是为光大圣贤之道而服务的,为利益天下苍生而服务的。所以,古代贤圣之心,是菩萨心无疑。
总体来看,《易经》展示的是理、象、数一体而变化不息的宇宙规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现象。圣人由此而“定人事”,也就是把这种规律与人类的思想行为联系在一起,为人类制定出一套与天地运行规律相应的和谐规则,形象地展示出来,由此而创立了八卦并进一步演绎出六十四卦。
每一卦,都有自己的象和数,以及蕴含的道理。从数的角度看,万物皆有定数,以数来定生死荣枯和吉凶悔吝;佛家称之为定业,只是佛家认为此定业非定业,故谓之定业。言外之意,业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体,否则整个虚空也容纳不下;它是可以改变的一个量体,权喻为种子和果实的关系。对于这样的一个数,孔夫子言,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意思是,五十五是诞生天地的数,五十是生化万物的数。
如果按照老子的说法,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去看,五十四加一,就是五十五。换句话说,1 + 54= 天地之数。其中,三生万物,故阳数始于三,极于九;所以乾卦“用九”。二三得六,地之半也是六,阴数成于六,所以坤卦“用六”。六乘九等于五十四,所以说乾坤之用数相乘加上一,就是天地之数,故圣人言“乾坤为易之门”。而再具体到乾坤两卦的策数之和,也正好是 360,为一年的天数。六十四卦的总爻数 384,就是太阴历闰年的一年天数。
你看,处处不离数,而人生长短之数其实难足百年!如何去度过这百年春秋?两千多年前的夫子已经为自己,也为后来的我们这不足百年之数做好了注脚。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再看看我们今天的人,说到对时间这个数的利用一点也不比古人差多少:从怀孕开始就有胎教,出生后有保姆、月嫂,二三岁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些老人教,之后幼儿园老师教,六岁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二十一二,再到硕士生、博士生二十七八,学得头昏脑涨,夸张点说是学富五车了。可到了三十岁,立没有立起来?立的又是什么?有人说成家立业,有人说立的是立礼。如果从成家的角度看,古人成家世间早,到三十岁已经有几个孩子了;现在人则越来越晚婚,三十岁没有成家的比比皆是。从立业这个角度看,许多人勉强维生,甚至还靠家里父母接济。
那么夫子的真意是立什么呢?我认为是立礼。在夫子看来,仁为体,礼为用。仁不可见,礼则明显可见。所以立礼,就是立本。南怀瑾先生说是为人处世的道理确定不变了,也对,也是立礼的意思。但若是兼及佛家的思想,我则觉得是立正信,信因果;否则孔子何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之语!后世所谓“富不过三代”之语,实是不积善德之果报。
到了四十岁不惑,就是没有疑惑,没有什么想不通,想不开的,人世间的一切,大自然的一切变化都清晰明了。明了的什么?明的是:自然是人心的外在显现,佛家所说的循业发现;易之两仪,所谓的阳,就是善念;所谓的阴,就是恶念。善恶交织,人生就是一部由自心所造作的因果史;而这部历史,唯有当下承担,不趋不拒,迁过从善,别无良策。
到了五十,知天命。知天命,就是明白天道,顺承天道,用儒家的话就是“明明德”,用佛家语就是“开悟”。悟了什么?借用禅门永嘉祖师的话:“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于是,有些人就说,梦是空的,六趣是空的,因果是空的。甚至有人不承认自己是男是女,有父有母,因为“空”了嘛。其实,梦就是梦,六趣就是六趣,因果就是因果,这个“有”(也就是佛家称之为色的东西)怎么能否定呢?不能否定,否定了就是偏执一端。人的执着来源于六根、六尘与六识,执着于此就是偏于有;可是,根与尘本空,即佛所言:“根尘同源,缚脱无二;识性虚妄,犹如空华。”同源就是同出于八识如来藏,能藏、所藏、执藏皆在其中。所以永嘉大师说:“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其实,这个“有”与“空”是一个,不是两个。所以说诸法无我就是空,为什么还要再去否定一个“人我”和“法我”;诸行无常就是空,不需要再去否定另外有一个“诸行”;清净涅槃就是空,可也并非一无没有的死寂之空啊。没有根、尘、识,心之体何以显现?所以《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哪里还有一个别的“空”、别的“色”?
可是,永嘉祖师又说:“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夙债。”怎么了?“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本来没有什么生与不生,灭与不灭,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忧喜。这个境界,勉强套用孔子所说,就是到了六十岁,耳顺了,听到什么样的话也不闹心,心静如水。能够做到这一步,一是见地到了,二是定力到了,所谓定慧等持。所以,“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议。”
如此一直下去,到了七十岁,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老子所谓“道法自然”,矩在其中,无心而和,即佛家的“任运自在”了。到了这一步,才算得上真的了啦。
月光童子
2016 年 7 月 4 日完稿于新西兰惠灵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