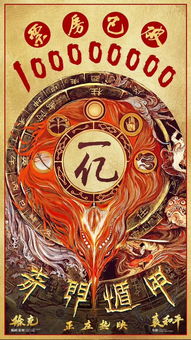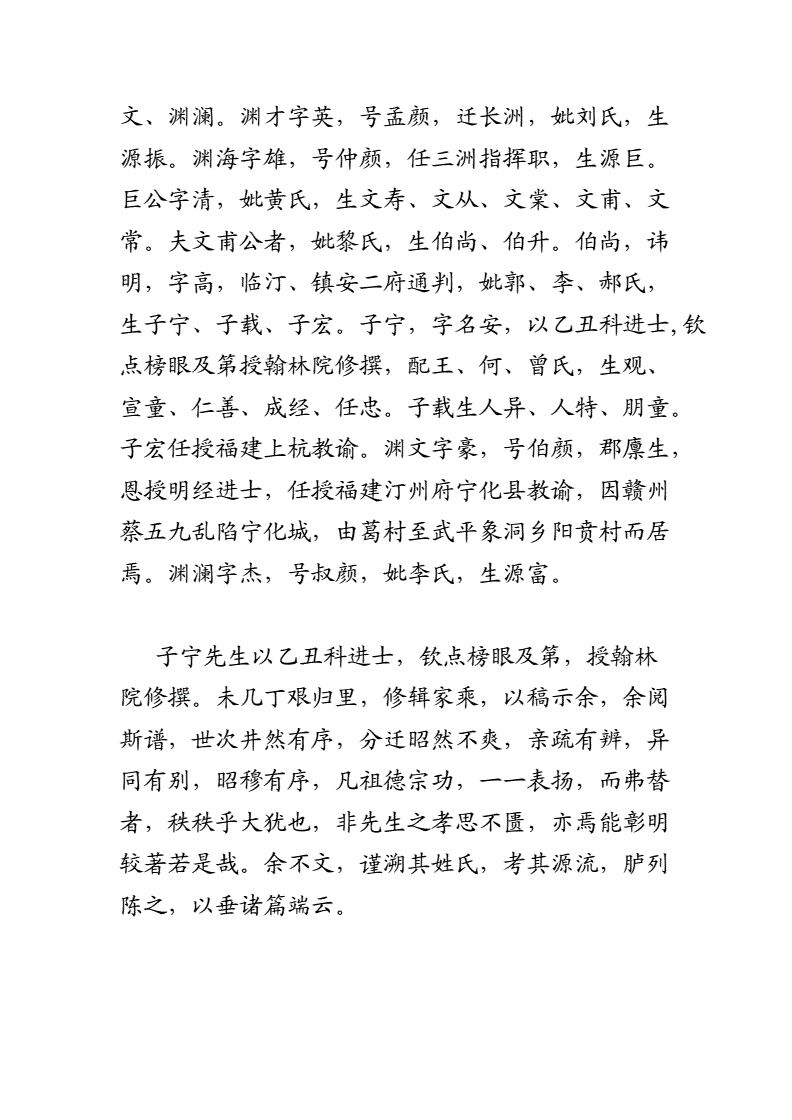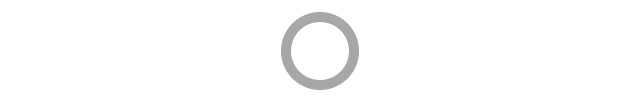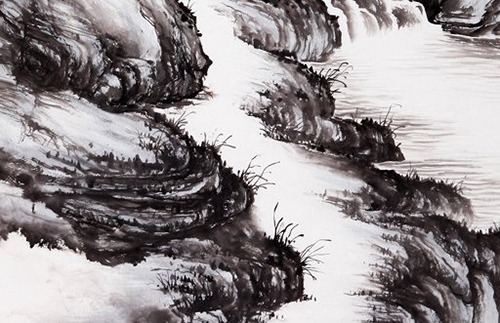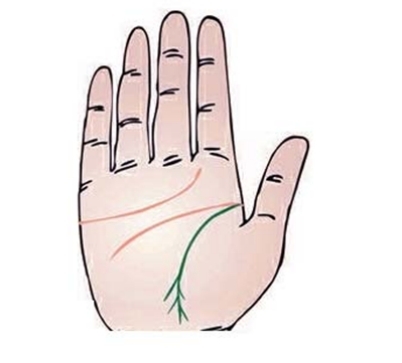“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
- 百科
- 2周前
- 336
“推”和 “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
命理师念鲜的微信:nianxiangege十三日的新闻上载着贵阳通信说,九一八纪念,各校学生集合游行,教育厅长谭星阁临事张皇,乃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冲去,于是发生惨剧,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其中以正谊小学学生为最多,年仅十龄上下耳。……
我先前只知道武将大抵通文,当“枕戈待旦”的时候,就会做骈体电报,这回才明白虽是文官,也有深谙韬略的了。田单曾经用过火牛,现在代以汽车,也确是二十世纪。

“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
汽车虽然并非冲锋的利器,但幸而敌人却是小学生,一匹疲驴,真上战场是万万不行的,不过在嫩草地上飞跑,骑士坐在上面暗呜叱咤,却还很能胜任愉快,虽然有些人见了,难免觉得滑稽。

十龄上下的孩子会造反,本来也难免觉得滑稽的。但我们中国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岁能画,两岁能诗,七龄童做戏,十龄童从军,十几龄童做委员,原是常有的事实;连七八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等于 “年方花信”的了。
况且“冲”的时候,倘使对面是能够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车会弄得不爽利,冲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敌人总须选得嫩弱。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

“身当其冲”,先前好像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这应验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婴儿杀戮”算是一种罪恶,已经是过去的事,将乳儿抛上空中去,接以枪尖,不过看作一种玩把戏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了罢。
十月十七日。

【析】 1933年6月至8月,鲁迅先后作杂文《推》、《“推”的余谈》、《踢》,同年10月又作《冲》。《冲》以“‘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 ‘冲’ 不可”数语,点明它的意旨,是《推》等文的承续和延伸,指出在黑暗中国支撑者们那里,冲是比推、踢更为恶劣的行径。
鲁迅的议论,针对贵阳惨案。报道惨案的“贵阳通信”,对惨案的背景、制造者和受害者、原因等,有概略介绍,认为,惨案是当局者“临事张皇”所致。鲁迅则在纷繁的事象中,独拈出惨案成因——“冲”,认为如此肆无忌惮地用“冲”来解决纷争,是绝不能释之为举止“临事张皇”的,相反,它是“深谙韬略”的“善于克敌的豪杰”所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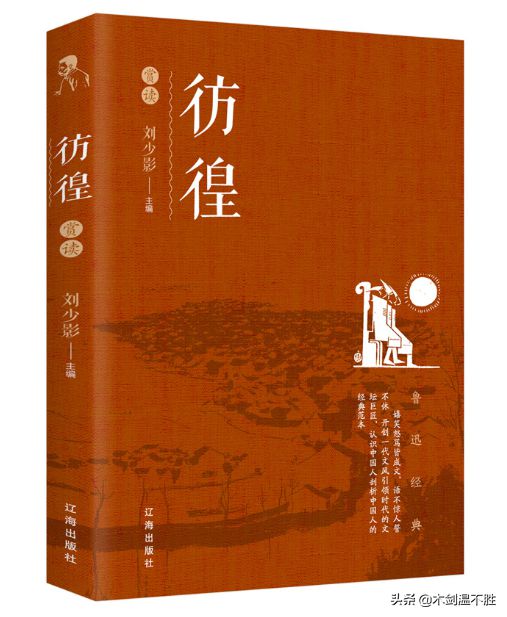
鲁迅指认“冲”并非“临事张皇”的表现,乃是一种韬略的运用,是以大量史实为根据的。战国时,齐人田单曾发明火牛冲锋的战术,出奇兵克敌制胜;沙皇为苟延残喘,也调动哥萨克马队冲击请愿群众;各国兵警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也常用水龙冲射来逞威。所不同者,中外古今用“冲”的韬略者,多为武将。现在,用“冲”制造贵阳惨案的,是为文官。文官袭用武将的韬略,就别有特点。他们面对弱小的学生,选用相应的克制器具: 20世纪 “并非冲锋的利器” 的汽车。而“冲”的结果,与水龙、马队乃至坦克的冲,是同样的有效。
但是,也因为是文官施展的韬略,与“冲”相伴而来的内具的滑稽,终难掩饰。这滑稽来源有二。一是惨案制造者行为的怪谬。他们身临民族危亡之际,不抵御外侮,却以纪念九一八的小学生为敌。二是惨案制造者心理的怪谬。他们先确认“十岁上下的孩子会造反”,丝毫不顾及自己心造的理论和社会常情常理是何等相悖。这样,鲁迅虽然没有直接剖析惨案制造者的行动目的和实质,但行为逻辑和心理逻辑的错乱,已使他们无可逃脱历史上的小丑和民族罪人的罪名。
能从一隅见全般,是《冲》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如题目所示,全文紧扣住“冲”运思着墨。然而,切入角度虽小,开掘却深。它在广阔的世界背景上作宏观考察,指出中外反动统治者的共性,是用“冲”的韬略对付“不恭顺”的人民。它又通过对贵阳惨案中“冲”的武器、对象、策划者的细致分析,展示出惨案制造者的特殊而复杂的个性: 他们集韬略与滑稽于一身,似乎聪明得计,实际愚顽不堪。文章因此具有涵概的广度,认识的深度,抨击的烈度。结构上,全文开端有冲和推、踢的明比,结尾有“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的应和,再顺此推测,杀戮婴孩既然不再是罪恶,恐怕将来有人会以此“玩把戏”,给人层层推进、浑然一体感。同时,也就有催人深思、警醒的艺术效果。
《冲》涌动着鲁迅式深切的愤怒。其表现形态,就是讽刺性语言的大量运用。鲁迅时而用和抨击对象极不相称的褒扬语言,如“威武的行为”、“克敌的豪杰”、“胜任愉快”等作反讽。以似提高实贬低,似赞美实斥责的反语技巧,凸现出反讽对象的荒诞、滑稽、可鄙。时而用切合对象特性的贬抑语言,如“一匹疲驴”、“敌人总须选得嫩弱”等作冷嘲。以形象化的描述,无情的戏谑式的嘲笑对象。讽刺技巧的穿插运用灵活变换,既使全文精炼耐思,也增强了行文的情感色彩和批判力量。